爱情悖论by凌凌子(爱情是一个卓越的悖论系统)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爱情是个人经验中最为特殊的部分,也是社会领域里最引人关注的话题。当代社会学家卢曼觉察到爱情现象的社会理论效益,从学术生涯之初就踏入了爱情这一研究主题。在1968年冬季学期代理阿多诺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席时,他选择了“爱情”为授课主题。
卢曼是德国社会学系统科学的代表人物,被誉为当代极少数几个改变了“范式”的社会学家。在考察了十七世纪以来爱情的历史语义学演化之后,卢曼配合知识社会学和交流媒介理论两条理论线索,为人们呈现了爱情作为一种交流媒介从社会中分化而出的过程。
近日,卢曼所著《作为激情的爱情:关于亲密性编码》的中译本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卢曼最受大【资 ;源 之.家.】众欢迎的著作,他在书中建立起的“爱情现象学”在他的系统论中具有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卢曼来说,爱情是一种概率极低的关系,一个卓越的悖论系统。人们一方面膜拜理想爱情,一方面又意识到其空洞。爱情的真伪无可交流,只能自我理解。不确定和高风险,既是爱情的悲剧之源,也是爱情的活力之源。爱情通过悖论机制发挥整合作用,让人学会适应悖论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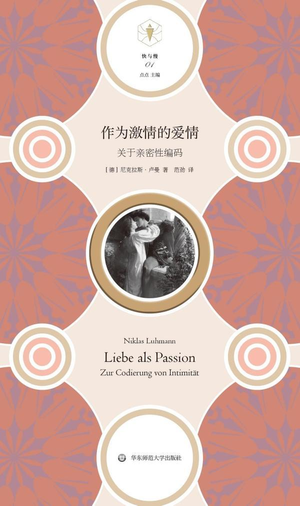
《作为激情的爱情:关于亲密性编码》
近日,本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范劲与《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汤拥华、广东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徐广垠、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余明锋、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华东师范大学六点分社编辑施美均一同做客同济大学云【资 ;源 之.家.】通楼,参与“作为社会技术的爱情——同济先锋哲学工作坊”圆桌讨论,围绕全新译作《作为激情的爱情》进行交流和分享。
卢曼呈现了爱情在“去中心化”之后的生命力
在汤拥华看来,近期被广泛关注的北大女生自杀事件不可避免地成为这次圆桌讨论的话题背景。他认为,这件事在今天的开放社会中的出现像是一个黑洞,给我们一种强烈的反差感,让我们意识到因为开放而变得安全社会中仍然可能存在风险。面对这样的事件,我们今天可能懂得很多爱情的常识,拥有开导他人的经验,也学过爱情心理学的知识,但是,汤拥华感叹说,“这些仍然不能使我们很好地过完这一生”。在他看来,我们理解爱情的理论努力,恰恰是卢曼之“系统内在的悖论”的表现;而我们应对这【资 ;源 之.家.】种悖论的方式,正是陷入这种悖论,即一方面明白爱情的不可理解,却另一方面仍然努力去理解它、想要去改变它。

圆桌讨论现场
徐广垠回忆了自己与范劲在柏林一起参加读书小组的往事。当时,他领读康德、黑格尔,范劲则领读卢曼;这是他对卢曼的最初了解。徐广垠认为,黑格尔和卢曼有极大的相似性。相对而言,黑格尔始终有一种“中心性”:黑格尔提出了一个纯粹形式性的、以悖论为开端的逻辑学,进而发展出一套辩证逻辑,但是,徐广垠指出,这个辩证逻辑本身是主体性和中心化的。黑格尔维持了辩证逻辑的自洽性,但主体哲学最后导致一种封闭性的结果。与之相对照,卢曼的优势在于从差异出发,直接承认复杂性。徐广垠解释说,在某些问题上,卢曼比黑格尔【资 ;源 之.家.】成功之处在于去中心、去主体化,这让卢曼的理论适用度更大、可操作性更强。
那么,与黑格尔哲学的对比,对于我们理解卢曼的“爱情现象学”意味着什么呢?在徐广垠看来,关键在于,一个中心性的主体化的哲学很难把爱情问题彻底讲清楚。这是因为,两个相互独立的主体之间产生的爱情哲学,比如黑格尔和康德讲到婚姻或者爱情的时候,会很容易陷入一种形式化、指导性的理论,从而忽视爱情的细节。相反,卢曼的系统论则能够呈现爱情在“去中心化”之后的生命力。
历史性的框架也不能穿透爱情的神秘
余明锋对徐广垠的看法表示赞同,他说:“读黑格尔法哲学里讲爱情你能够理解什么是爱情,但是没法学习怎么谈恋爱,但是卢曼的书有非常具体对爱情经验的描述。【资 ;源 之.家.】”徐广垠补充说,黑格尔的开放性是研究论题的开放性,但是卢曼本身就是开放的,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元理论”。
胡春春认为,相比于卢曼,他更愿意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的概念来理解爱情。这意味着,将爱情的社会性理解为资本;如果对爱情进行学术讨论,就是讨论这种资本在具体的语境中如何估价。当然,爱情的社会性总是具有一种神秘性,这也吸引这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进行艺术创作。对于汤拥华指出的理解爱情的“悖论”,胡春春认为,唯一“卢曼式”的讨论方式,是把卢历史框架性的讨论;这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对爱情本身进行讨论,但可以把爱情的发展史、爱情故事放在一个历史性框架里进行展现,不过胡春春强调,这还是不能帮助我们穿透爱情【资 ;源 之.家.】的神秘性。
“爱智慧”:哲学与爱情
汤拥华补充说,恋爱也许就是比其他的活动包含更多的反思过程。他发问:“一个人可不可以真的在谈恋爱,而不是搞清楚爱情是什么?”余明锋赞同:“爱情是自我反思性的过程。”范劲则认为,哲学就是这样的一种反思形式。余明锋对此补充说,“哲学”一词的古希腊语原意就是“爱智慧”。
余明锋讲到自己经常和学生说,哲学是“深渊”上的学问:“科学是实证学问,哲学是反思学问,永远在深渊上盘旋,不会轻易下论断,所有的结论都会被再反思。”在他看来,爱情也有高度的反思性和深渊性。爱情是自我的整全性的出让,这意味着,“只有对方在场你才能感到完整,真正恋爱就是找另一半,你自己不再是一个整全。某种意义上【资 ;源 之.家.】,爱情使人变成高度神经质,疯狂成为常态。”余明锋认为,上述女生自杀事件中的男生没有在爱,而是在强烈地表达占有欲。问题在于,这种占有欲正是通过一个爱情的模式给对方带来幻觉,让对方受到指控、不断自我反思。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
余明锋谈到巴塔耶的《情爱论》,据他介绍,巴塔耶将爱情与宗教、献祭、暴力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在巴塔耶的视角下,爱情和死亡有某种相似性。余明锋说:“爱情的体验有生本能和死本能的交织,这样的权力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爱情这个系统自身所具有的危险性。”
施美均则联系起“轻与重”系列丛书中的另一部著作,巴迪鸥的《爱的多重奏》。在书中,巴迪鸥提出两个人的恋爱其实是最小规模内的实现的一种“共产主义【资 ;源 之.家.】”。之所以称之为“共产主义”,是因为这种恋爱坚持把爱情中的偶然性一直坚持下去。施美均认为卢曼是在用非常技术性的方式讨论爱情,巴迪鸥跟卢曼比起来显得很天真。在施美均看来,卢曼向我们揭示了亲密关系悖论系统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内在同构,这意味着,在现代,爱情被驱赶到“私领域”当中,从而和“公领域”分开了。


